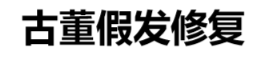申奥执导,刘昊然、王传君、高叶等实力派演员主演的电影《南京照相馆》在全国各大影院上映,且引起观众极大反响。影片讲述了1937年冬南京沦陷后,七名南京百姓躲进吉祥照相馆避难的一段经历。当照相馆被迫为日军故事便围绕着这群本只为苟全性命的人展开。他们在生死边缘徘徊,却毅然决然地选择保存这些记录日军罪行的照片。影片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无数观众沉浸其中,被深深触动,不禁潸然泪下……
影片《南京照相馆》:不少镜头都是按历史照片1:1复原的,有暴行真相,也有“亲善”假象
本文讲述的并非影片中的故事情节,而是一个真实发生的《南京照相馆》的故事。其实,影片中照相馆的原型并非“南京照相馆”,而是“华东照相馆”。它坐落于南京老城区估衣廊的街道之上,毗邻长江路。这里既是当时民国政府总统府的所在地,亦是南京市颇为繁华的商业区之一。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惨案。三十余万中国平民与被俘士兵惨遭集体枪杀、焚烧、活埋以及其他残忍手段的迫害,南京市约三分之一的房屋被付之一炬,几乎所有的商店皆被洗劫一空。时,一个叫罗瑾的男孩儿,随一家躲进“难民区”,逃过了这场劫难。1938年1月,不到15岁的他到一家新开张的“华东照相馆”当学徒。
1938年1月上旬的一天,有个日本鬼子少尉军官,拿了两个120樱花牌胶卷来到照相馆要求冲印照片。账房“舅爷”不经意间收下胶卷,并告他三天后来取。次日午后,当罗瑾将照片冲印而出时,眼前的场景令他触目惊心。拍摄的画面无一不是日军屠杀中国人的惨状:被砍下的头颅整齐排列,仿佛在无声控诉着暴行。活埋平民的残酷瞬间,定格了生命消逝的绝望。还有日军对妇女施暴的罪恶场景,尽显人性的丑恶…… 罗瑾赶忙将此事告知舅爷,却被舅爷再三叮嘱,务必缄口不言,否则必将招来灾祸。
小小年纪的罗瑾,不知哪来的勇气,趁其旁人不注意,匆忙将底片拿到暗室印相,夜里悄悄用毛巾揩干,晾在案板角落上。待天亮后,他将照片装入纸袋,把纸袋贴在角落案板下方,并用胶布横竖交叉固定妥当。此后,但凡有日本人前来冲印照片,他必定仔细审看。一旦发现记录鬼子烧杀奸淫的照片,便偷偷印出留底。就这样,他先后积攒了30余张。多少年后,罗瑾回忆道:“我深切知道,照片是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的,一定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将这几张鲜血淋淋的照片想办法保存下来。”
罗瑾还亲手做了一本小相册,从积攒的照片中悉心挑选出16张极具代表性的,郑重地放入相册之中。他在相册封面左上角绘就一个深红色的心形,右下角则画了一把日本军刀,那军刀已深深刺进心脏,心的下方坠着五滴鲜血。此外,他还在右上角写下一个方形的“耻”字,下面打上一个“?”号。后来他向人们这样诠释了封面图案的寓意:“为了纪念这些死难的南京父老兄弟姐妹,我将画面上的心、刀、耻都勾上了黑边,‘耻’字是颤抖形的黑边,以表达我沉痛的哀悼。” 为防止大屠杀的真相败露,日军随后搜查南京市内照相馆。罗瑾不得不将照片多次转移和藏匿。
1940年5月,17岁的罗瑾考进了汪伪政府的“汪伪交通电讯集训队”,驻地在南京毗卢寺。他与100多个十八九岁的年轻人,白天学发报、学旗语、学架线,夜晚就睡在毗卢寺内的佛堂里。开始罗瑾认为此地安全,便将相册藏在自己的床下。岂料,1941年初,同驻扎在毗卢寺内的伪宪兵二团培训学员为迎接汪精卫来训话,对驻地进行了一次安全大检查,且在检查中发现了一颗来历不明的手榴弹。于是乎,便开始在全寺进行了大清查。情急之下,罗瑾在茅房的砖墙上掏空一个洞,将相册塞进去,并糊上泥巴。岂料,几天后罗瑾发现相册竟不翼而飞。为防不测,罗瑾便逃离了南京,先后在苏州、上海、青海等地辗转......
原来,罗瑾的那本相册落到了他的同学吴连凯手中。一天早晨,起床号尚未吹响,吴便起身直奔后院的厕所。当他走进茅房,发现在砖墙脚下的茅草丛中,有一个灰蒙蒙的东西。这是一本用硬纸装订的巴掌大的相册。翻开后,16张二寸半的照片令他不由得毛骨悚然,连上厕所也忘了。他似乎突然意识到了什么,朝四周张望无人后,便将相册塞进怀里。
考虑到日军对寺庙搜查较少,且佛像被视为神圣场所,相对安全,故相册的第一藏匿点设在了毗卢寺大佛的底座夹层中,该寺供奉的毗卢遮那佛高约5米,底座中空。第二藏匿点设在了家中隐蔽处,先后藏于屋顶瓦片之下、厨房灶台的暗格之中以及床板夹层里,其中藏在床板夹层的时间最长,达1年之久。在日军大规模搜查期间,他还曾短暂将相册放入皮质公文包,因为该包为伪政府职员身份的象征。1942年后,吴连凯最终将相册用油纸包裹,缝入冬季厚棉被的棉絮夹层中。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2月15日,南京成立了“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任命石美瑜为庭长。8月1日,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时任日军第六师团师团长的谷寿夫被押到上海受审。然,在庭审中,但当法庭问及南京大屠杀事时,他则时而装糊涂,时而又说没有听说过,还推脱说:“1937年12月21日我奉命到芜湖,在南京只有一个礼拜,没有听说屠杀消息。” 如此等等。战犯处理委员会第38次常委会认为,谷寿夫系“南京大屠杀”之要犯,决议“移本部军事法庭审判”,即将谷寿夫从上海押至南京审判。时,南京号召市民揭发谷寿夫部队罪行的布告贴满了全城。南京市民成群结队地涌到临时调查庭,哭诉埋藏了近10年的血海深仇。
时,更名为吴旋的吴连凯,在布告下伫立良久,若有所思。次日清晨,他郑重地取出那本已悉心藏匿6年之久的相册,小心翼翼地将其揣入怀中,而后迈着沉稳的步伐,一步一步地朝着位于新街口的南京市临时参议会走去。当吴旋向接待者讲述了自己的来意,以及这6年来为保存相册所经历的种种艰辛。当参议会接待者翻开这本相册,里面记录的日军暴行画面如同一把把利刃,直击人心,他们完全被震惊了。随后,吴旋被要求写下相册的来历以及他的亲身经历。他缓缓铺好一张红色竖格的朱丝栏笺纸,也就是俗称的“十行纸”,奋笔疾书写下了“为呈献南京大屠杀案敌寇罪行照片事”的呈文。在呈文的末尾,吴旋重重地按下一个很大的手印,那手印仿佛一摊殷红的鲜血,饱含着他对那段惨痛历史的悲愤与控诉,也承载着无数死难者的冤魂与哀伤。
窃民于民国廿六年日寇发动淞沪之战未几而攻陷南京时,民仅十五岁,且阻于交通,躲避难民区。时有洪姓(应为罗姓)学友于南京开设照相馆,有日寇以其所得照片至该馆洗印,俾作“胜利”之夸口。该同学惧其淫威,不能拒绝,乃同时用其底片加印一份,共得小照片十六张,多为敌兵之罪行,或以残杀我同胞为笑乐,迄今视之,犹有余悸,其后洪某(罗某)以日兵搜索,未敢留存,乃由民保管,经无数困苦,始终未忍遗弃,以便将来供与敌人清算之资料。胜利以来,此十六张照片始得重睹天日,今闻贵会有搜集敌寇罪行、侦讯战犯用,特将该项材料检出,请代送有关机关,使残暴敌寇得以明正典刑。并请审讯完毕仍将原片赐还,以作纪念,实为德感。
南京市临时参议会秘书处秘书长肖若虚不敢怠慢,遂作为急件写成公文“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
……据市民吴旋呈称:旋在民国二十六年未及退出南京,当由友人处获得敌寇自行拍摄之日军残杀及奸淫我南京同胞之照片一册,共十六张,现闻日寇战犯已引渡至京审讯,特呈请转送有关机关备作证据等情,查该项照片确系日寇施行暴行所自摄,而足为证实战犯罪行之铁证用,特抄具原呈,连同照片送请查照附作物证之一部,至将来审讯定谳以后仍希将原件赐掷,以便检还为荷!
1947年2月6日,“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南京市黄埔路(中山东路口)“励志社”(现为钟山宾馆)黄埔厅大礼堂,对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开庭公审。在如山铁证面前,谷寿夫再也无法狡辩抵赖,只得俯首认罪。3月10日,法庭即将作出庄严判决。尽管吴旋早早便赶到了“励志社”大礼堂,然而,2000多个旁听席早已座无虚席。他只好与众多民众一道,伫立在大门之外,静静地通过大喇叭聆听庭审的实况。当石美瑜庭长铿锵有力地宣读《战犯谷寿夫判决正本》的声音传来:“根据《海牙陆战规例》、《战争罪犯审判条例》,作出判决:谷寿夫在作战期间,共同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抢劫,破坏财产,处死刑。”,刹那间,法庭内外欢声雷动。几乎所有人都霍然起身,纵情欢呼,宣泄着积压已久的悲愤与仇恨。此时此刻的吴旋,喜极而泣,泪水夺眶而出。他期盼已久的这一天,终于来临了,正义的审判为无数死难者讨回了公道。
1947年4月26日,谷寿夫的末日到来了。行刑前,他借来剪刀,剪下了自己10个指头的指甲和3束头发,装在用白手帕做成的小袋子里,留给家人,并留绝命诗一首:
上午11时30分,特由该庭将被告谷寿夫验明正身押送雨花台刑场,依法枪决。当日,吴旋早早便静候在刑场,神色凝重而又带着一丝期待。他亲眼见证了南京大屠杀刽子手谷寿夫的末日,这个双手沾满无数无辜百姓鲜血的恶魔,终于受到了正义的制裁。遗憾的是相册的制作者罗瑾未能亲眼见证这一切。
这本由罗瑾制作、吴旋保存的相册,因其关键作用被法庭列为京字第一号证据,成为南京大屠杀最重要的物证之一。尽管审判过程中,除这本相册外,法庭还采纳了许多由外国人士拍摄的照片和影像作为证据,如约翰·马吉、明妮·魏特琳等冒着生命危险用相机和摄影机记录下日军的暴行,但罗瑾和吴旋守护的相册在其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
1953年,罗瑾投靠子女定居在福建大田县。1955年,他在大田县城关镇开设一所“上海照相馆”,且成为当地知名照相馆,直至上世纪80年代退休。因解放后政治运动频发,小心谨慎的罗瑾从未提及过相册照片之事,甚至连家人亦不知情。直到1982年日本教科书事件后,南京市政府征集大屠杀史料,看了报道的罗瑾于1983年初向福建大田县政协首次书面说明经历,后转呈南京有关部门。1983年4月,南京市档案馆接收罗瑾陈述材料后,核查“京字第一号证据”来源时,通过相册封面特征和华东照相馆馆标,确认罗瑾为制作者,并告知罗瑾有关吴旋献册细节。据其子罗文回忆:“父亲得知后痛哭失声,说历史没有辜负那些死去的人”。
1987年12月,南京大屠杀纪念日活动期间,由南京作家谢光宁编剧,福建电影制片厂导演罗冠群执导的影片《屠城血证》在全国公映。福建和南京两个电影厂合拍这部影片的原因之一,便是影片中照片故事素材的原型为已在福建定居的罗瑾。影片上映后,罗瑾受邀在福建大田影院观看,但未公开评论影片与自己的关系。然,他观影后私下留言:“故事不同,但那些照片是线周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特邀罗瑾作为证人出席活动,这也是罗瑾当年逃离南京后第一次重返故土。他在晚年自述中称:“想再看一眼当年藏相册的厕所墙,告诉那些亡灵,有人记得他们。”
影片《屠城血证》与《南京照相馆》中的照片故事均取自同一素材:演员可都是老戏骨
同年4月,在纪念馆组织的证物守护者座谈会上,时年72岁的罗瑾与75岁的吴旋首次相见。1946年献册时,吴旋任南京市临时参议会秘书处文书。解放后曾任南京某国营厂工会干部直至退休。两人见面的地点在位于南京江东门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纪念馆专职摄影师郭晓江为两人拍下了这张合影。据摄影师回忆:“吴旋拄拐杖先到,罗瑾进门时两人对视良久,突然同时喊出是你!。拍照时罗瑾紧握吴旋手腕,吴旋另一手指向展柜里的相册复制品。” 合影的背景为纪念馆“史料陈列厅的证物展柜,玻璃反光中可见相册复制件的轮廓。两位老人身着深色中山装,胸前别着历史见证人”绢花。虽然笔者未能找到这位摄影师拍摄的照片,但找到了另一张两人在纪念馆合影。
吴旋见到罗瑾的第一句话是:“原来那颗‘耻’字是你刻的,我守了它六年。” 然,当年吴旋发现相册前,相册如何从厕所墙转移至草丛的,至今仍是未解之谜。这是两人在1940年底分别55年后的第一次见面,也是他们人生中最后一次的“同框”。吴旋于1998年去世,享年74岁。罗瑾于2005年去世,享年82岁。今日他们用生命守护的那本相册静静地珍藏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2015年10月9日,它与国内其他南京大屠杀档案一同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铭记的历史遗产。
罗瑾和吴旋的故事,以及由此改编的电影《南京照相馆》,给予我们诸多超越历史本身的思考。两位普通青年在民族危亡时刻的抉择与坚持,展现了人性中最可贵的光辉,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也有人愿意为真相和正义挺身而出。正如相册封面上那个巨大的耻字,它不仅是历史的血泪控诉,更是对后世永恒的警示:真相可能被暂时隐藏,但永远不会沉默。j9九游会入口